在那个时代,“不食周粟”同样是因少而可贵:“四海归周莫不臣,首阳山下饿夫身。清风万古何曾死,愧死当时食粟人。”如果要进一步区分遗民与隐士的话,则这部分人更重的是遗民族色彩,他们更多的是伤悼故国疏离新朝,而非避世隐逸。尽管黄溍《送吴良贵诗序》说方凤、谢翱、吴思齐“三先生隐者”,起码在宋亡之初,还不太像隐士。他们到处举行各种悼念故国的活动,抒发对故国的哀思,而非隐居于园林或山间林下,其生活状态及心态,也绝无隐逸之士之“逸”。即使是所谓隐于黄冠者如郑思肖、汪元量也是如此。其诗其文,总是无限的故国之思,贯注着太多又太浓重的愤激、痛苦和哀伤,或者无可奈何的悲凉,满纸麦秀黍离之感。如林景熙之《题陆放翁诗卷后》:
诗墨淋漓不负酒,但恨未饮月氏首。床头孤剑空有声,坐看中原落人手。青山一发愁濛濛,干戈已满天南东。来孙却见九州同,家祭如何告乃翁。
这不隐士诗。隐士诗是平和的,恬淡的。如仇远序马臻诗所言:“大抵以平夷恬澹为体,清新圆美为用。陶衷于空,合道于趣,浑然天成,不止于烟云花草鱼鸟而已”。正如
锺嵘评陶渊明:“笃意真古,辞兴婉惬。每观其文,想其人德。世叹其质直,至如‘欢言酌春酒,日暮天无云’。风华清靡,岂直为田家语耶?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。”
此为隐士诗。这一代人中被视为元人且被视为隐逸之士的,有仇远、白珽、黄庚、赵文、戴表元、袁易等。这些人中多有在宋亡若干年后曾出为教职的,但他们基本上都具备隐逸之士的心态。如白珽,入元后曾以遗民自居,与宋遗老徜徉于西湖之滨,参与月泉吟社,拒不汪元量《水雲集》卷一《醉歌》其十。出仕,诗名益著。尽管一度出任教职,后迁婺州路兰溪州判官,但“日与韵朋胜友曳杖游衍,衔杯赋诗”。终生以诗人自命,临终嘱其子,墓碑惟题“西湖诗人白珽之墓”。
在后人眼中,他们是遗民,是隐士。清代全祖望云:“月泉吟社诸公,以东篱北窗之风,抗节季宋,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,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,可谓壮矣。”
说他们是陶渊明那样的隐士。袁易也曾为书院山长,既而辞归,黄溍为他做的墓志铭,描述的是一位隐逸之士的生活:行中书省署君石洞山长,君乃欣然就职。既归,卒隐弗仕,即所居西偏为堂,曰静春。壅水成池,周于四隅。池上累石如山,芰荷蒲苇,竹梅松桂,兰菊香草之属,敷荣缭绕,而其外则左江右湖,禽鱼飞泳于烟波莽苍间。堂中有书万卷,悉君手所校定。客至辄敛卷,相与纵饮剧谈,留连竟夕乃已。君丰姿秀朗,每雨止风收,挟小舟以笔床茶灶古玩器自随,逍遥容与,扣舷而歌,望之者识其为世外人。
相关文章:
声明: 本文由( admin )原创编译,转载请保留链接: https://www.hxlww.net/15416/hxlwfb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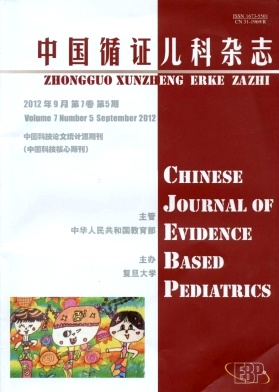

近期评论